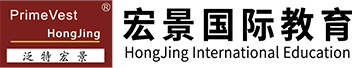行医是少数需要纪律、奉献和牺牲的职业之一。
然而作为人类,这些特征往往与我们的社会和情感需求是不兼容的,当到达了我们所能承受的极点,就会开始顺服呼召的决定。几个月前,一个朋友和在另一个科室的同事跟我提到,在结束一天漫长而紧张的工作后,她不得不在路边把车停下,因为她无法压抑想要哭泣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开车。
每年近400名医生死于自杀。当医学界开始密切关注筋疲力尽、抑郁的症状和体征时,发现低落就在我们身边。我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原因,发现我的身体也存在这样的症状。
当我在剑桥健康联盟(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参加住院医师实习培训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项目的导师告诉我们要关注其他实习生,确保我们这八名精神科的实习生,能成为彼此的依靠。出于本能,对于我们需要保护对方些什么感到十分担心。
然后我终于理解了。
在成功匹配到她梦寐以求的搭档后,另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可怕的住院医师经验,教会她如何变得坚强和自信。她从逆境中学习、成长。不过我在想,在这个过程中她被偷走了什么呢?我想知道,如果在这个过程成中,她是一帆风顺而非逆境存活,作为医生,她能走多远。
在我面试住院医师项目的时候,被反复问到是否喜欢医学学校——长时间的学习时间,需要掌握的大量信息,临床工作的繁忙和紧迫。我的外交式回答是: 我很感谢这次机会,但是我很高兴不需要再重复一遍。它掩盖了肮脏的小秘密:医学是最好的,而最坏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忍受极度的孤单、气愤、耻辱、或者伤心。
因为,“没关系的,我就要成为一名医生了。”
我现在是做住院医师第一年,我不断地被提醒要密切关心我的同事——成为我的合作住院医师的监护者。
这一次,我告诉自己,我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我读医学的第三年后期,一位同学含泪倾诉她毁在一个严厉的监督医师的手上。我跟她说都会好的,我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狠心不理会她的悲伤是因为太难以想象培训的残酷现实。我失去了对一个困境的同情,而这个困境同样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像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肯尼恩学院他的毕业演讲中提到的幼鱼。当被大鱼问到“水怎样?”时,幼鱼好奇地问道:“水是什么?”
幼鱼们看不出超出他们现有的境况从而理解更大的画面。当轮到我们参加培训的时候,我将是未来医生中的一员,努力认清什么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什么不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处在这个混乱当中,而且我们拒绝找机会去认清什么是痛苦,因为我们全部人都接受了它是成为一名临床医师的艰难道路中的一部分。成为一名医生也是如此。
经历了长时期的与脑癌的斗争,已故作家Alison Piepmeier 回顾他在临终护理的经历,问道:“我怎么在这里生存,在这里我这么高兴也这么伤心?”这是当我从一名医学学生成为新毕业的医学博士的10年里,每天以不同形式摸爬滚打的最切合的问题。
除了医疗界可以一些应对措施来减少抑郁的发病率,我想,我们所有人,作为这个团体中的成员,必须要自己维护我们的心理健康。
今年的早些时候,我写了一些关于在医学中寻找快乐的文章。有两名医生开玩笑地在推特上跟我提说,在历经头一年的蹂躏后,他们很期待看到更新。“失去快乐”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华莱士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意识---意识到什么是真实的和必要的,如此隐藏在我们眼前的情景中,以致于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这就是水,这就是水。’”
这就是我们的水---我们的职业需要照顾别人。我们需要照顾自己。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彼此照顾,有同理心和理解。支援幸存者。做其他人的监护者。
宏景作为高端医疗人才培训机构,与美国500家医疗机构合作,不断的输送高端医疗人才海外就业。打造最适合中国考生的授课方式确保最短时间内通过考试。专业移民顾问助您最快移民。精品课程包括:美国医生、香港医生、美国牙医、美国中医、医学检验师等。
(译者:Alice、侯菲菲)
声明:本文系宏景编译自STAT NEWS,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译者。